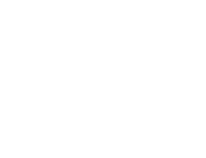大道如砥 行者无疆——BDAE专访Patrick Hopkins
近日,MSH CHINA 联合创始人Patrick Hopkins接受德国BDAE(Bund der Auslands-Erwerbstätigen)专访。他出生在美国,却钟情亚洲文化,空军退伍后在战乱地区为非政府组织工作多年。后来,他移居印度尼西亚并进入金融保险行业,在中国创办了一家成功的国际健康保险服务公司——MSH CHINA。这次采访是对Patrick生平的一次特别回顾,也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时间旅行。
Q 您出生在美国,您会如何描述自己的童年?
Patrick:我出生于1947年,那是杜鲁门总统执政的年代。十岁时,我随父母从芝加哥搬到了附近的郊区。我还记得,威廉姆斯湾有一个巨大的湖泊,风景如画,吸引了许多芝加哥的富人来度假。那时候,小镇只有1500名居民,民风淳朴,几乎每个人都认识彼此,我和我的六个兄弟姐妹可以一直在外面玩耍,只需在午餐时回家就可以,我在那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我14岁的时候,我的父亲从区域销售经理晋升为公司总部副总裁,分管销售和市场,我们全家从威斯康星州搬家到康涅狄格州纽约附近的新镇。这次搬家对我影响很大,因为美国中西部和东海岸之间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威斯康星州的移民主要是1848年革命失败后逃往美国的瑞典人和德国人,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康涅狄格州则更加多元化,也更富裕,纽约附近是一个真正的文化“大熔炉”——意大利人、希腊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犹太人以及许多东欧人都聚居于此。虽然我在那里度过了我的高中岁月,但如果有人问我来自哪里,我的根在哪里,我会说,是威斯康星州的威廉斯湾。
Q 对您来说,搬到康涅狄格州是一种文化冲击吗?
Patrick:其实没有那么夸张,不过是少年的我,在转校以后交不到新的朋友,很想念故乡的伙伴。上大学以后,我没有好好学习,不过我有自知之明,所以我退学了,没有继续浪费时间和我父母的钱。
Q 当时,越南战争已经在进行,许多年轻人被征召入伍。
Patrick:在我高中,甚至刚上大学的时候,都很少人关注战争,直到1967年初才变得严峻起来。那时情况是,如果上了大学,可以推迟服役,不会被征召入伍。这对富人是有利的,他们总能生活在安全中,世事就是如此不公。当时,80%到90%的年轻人被征召参加越南战争。但刚出校门的年轻人都是懵懂的,对社会一无所知,大部分的人在参军之后才慢慢成熟起来。我一向擅长分析,如果我不主动出击做点什么,就得去越南了。再三思量下,我选择申请加入空军,因为空军在通过测试后可以申请行政类工作,这样就没有人向我开枪,我也不必向任何人开枪了。
Q 那能确保您不必去越南了吗?
Patrick:没有百分之百的确定性。我考上了空军,成为一名莫尔斯电码操作员,我们基本上是轮班工作,有时候白天,有时候晚上,我会听电码然后转录下来,就像一只坐在空调办公室里的猴子。经过9个月的培训后,我和我的同伴被派往土耳其,进行为期18个月的首次海外任务。1968年,我被调到了日本冲绳岛的一个监听基地工作。那时候冲绳群岛还是被美军占领,直到1971年才归还给日本。
Q 从土耳其到日本,是您与东亚文化的第一次接触?
Patrick:是的,这也是我后来去亚洲的契机。在日本的经历非常有趣,我甚至学了一点日语。1970年,我退伍后回到美国的康涅狄格州上大学,选修了我非常感兴趣的中东和东南亚历史课程。我不是为了毕业文凭,只是凭兴趣选择想学习的学科。
Q 那您学习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Patrick:因为战争的影响,我已经整整耽误了四年的时间了。我想成为类似《纽约时报》这种媒体的外国特派记者,所以我申请了两所新闻学院,一所是东京上智大学(Sophia University),另一所是菲律宾大学马尼拉分校。令我惊喜的是,两所学校都录取了我!当时,菲律宾的政治局势不稳,随时可能戒严,而我又钟情于日本文化,于是我选择了东京。没想到后来学校关闭了新闻专业,我就转读东亚研究专业,并获得了硕士学位。我想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但我也知道,在日本成为大学教授的机会微乎其微。
Q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Patrick:当时,美国政府正在物色像我这样能掌握日语的美国人,我轻松进入了第三轮面试。但我清楚意识到,这份工作不适合我。我不愿意成为一个无足轻重、没有任何影响力的螺丝钉,一辈子坐在那里听日语、翻译文件。最终,我去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天主教救援服务,虽然薪水远不及政府工作,但能帮助到孩子们。后来,我去了当时处于动乱的印度尼西亚,为营养不良的儿童和母亲提供食物,开展农村扶贫项目,帮助当地人养鸡养鸭,生产农产品,提高他们的收入。
Q 看到这么多的贫困和挨饿的孩子,会引发您内心的触动吗?
Patrick:我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帮助当地组织成长,并确保资金和食物送达需要的地方,帮助到更多的人。工作本身非常充实和有意义,只是在东帝汶的经历却让我感觉到很痛苦——这段历史可能很多人已经不记得了。
Q 您是指1975年的东帝汶冲突,导致了现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饥荒之一吗?
Patrick:是的,那里的人饱受苦难。在起义期间,葡萄牙殖民统治者几乎一夜之间就离开了,印尼军方无法控制局势,整个国家完全失控了,无数人死亡。我的上司弗兰克·卡林是一位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坚毅果断,在当地积累了极佳的声誉,因此也得到了当时印尼军情部门的负责人本尼·穆拉达尼将军(他本人也是一位天主教徒)的看重,最后只有我们救援服务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被允许进入东帝汶。我跟随弗兰克在后方协调复杂的物流安排,签订驳船和登陆艇的合同,购买卡车和租用直升机,运送了成吨的食物和药品,帮助了数以百万计的难民,这让我非常有成就感。
Q 您的下一站是哪里?
Patrick:在1984年之前,我都在亚洲为救援服务委员会工作,我对亚洲文化的迷恋与日俱增。1982年,我去了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帮助因苏联入侵而离开故土的阿富汗难民。我们到达巴基斯坦后,对当地井然有序的安排印象深刻。当地政府并没有按照通常惯例让数十个救援组织共同支援一个体量庞大的难民营,而是划分了多个小的难民营,每个难民营都分配了一到两个救援组织,这样我们只需要专心帮助一个难民营就可以了。在那里,我和很多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合作,有支持哈扎拉族群的奥地利阿富汗难民救援委员会、喜马拉雅山脉北部的阿迦汗基金会,巴基斯坦的天主教教区,那是非常有趣的一段经历。
但在不知不觉间,天主教救援组织也发生了变化。我刚加入的时候,像我这样的项目经理或驻外代表,基本上都必须是天主教徒。到了80年代,机构越来越依赖非神职人员。1984年,我的上司被换掉,新任的东亚区域总监是我在东帝汶项目期间相处不好的一位神父,我知道是时候离开了。
此外,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需要西方援助组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Q 但您没有回到美国。
Patrick:确实,我想留在亚洲,我的根在亚洲。一开始,我留在巴基斯坦为美国国际发展署工作。但我感到非常挫折,很多美国顾问非常傲慢,这里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工作,只是为军方服务,支持沙特和巴基斯坦在阿富汗战争中对抗俄罗斯。我变得愈加愤世嫉俗,我也认识到,大型西方援助组织实际上都是为政治服务——即使他们自己从来不承认。我还收到一份马尼拉亚洲开发银行的工作机会,薪水丰厚,有大房子和优渥的养老保障。但我将成为一个庞大官僚体系中的一个小角色,必须在不断的交际中脱颖而出,而这并不是我的强项。后来,我碰巧重新联系上了一位旧同事,他在一家维也纳的金融保险服务公司工作,为世界各地大使馆的美国外交官提供金融保险,他为我推荐了这份工作。
Q 您没有经验,也没有学过经济学,为什么有信心成为一个理财顾问呢?
Patrick:确实,大家都觉得我太疯狂了,放弃稳定高薪的工作,去做一个没有固定的收入,自己支付办公室和差旅费的金融保险代理人。但我知道,销售的工作本质上就是做一个好的倾听者,找出对方需要什么,再去满足这些需求。
后来我发现,最好的目标客户并不是美国外交官群体,而是海外国际学校老师。他们脱离了美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再有资格领取美国的养老金,他们的需求有缺口。大部分学校会雇佣教师夫妇,这样只需要为两个人支付一份房租。这意味着,这些夫妇可以靠一个人的工资生活,将另一个人的工资投资到储蓄和理财中。我为将近1,000位教师建立了储蓄计划,每月存800到2000美元,我赚取了源源不断的佣金,而且还无须全年工作,因为他们通常在夏季和圣诞节期间会回母国度假。我一直在金融保险业工作了16年。
Q 那时您已经财务自由,不需要继续工作了吗?
Patrick:是的,那时我已经52岁了,常年往返于雅加达、马尼拉、北京、上海、大阪、东京等地,拜访不同的国际学校。我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出差,没有个人的生活和社交圈子,幸好那时候我没有孩子需要照顾。虽然我很喜欢我的客户,但是老是和相似的人打交道,让我觉得失去了挑战性。我问自己,为什么不深耕一个市场,探索更多可能性呢?最后,我选择了上海,一个当时拥有2000万人口的大都市,我需要有当地人帮助我,所以我找到了Celine,她也是现任MSH CHINA的CEO,剩下的大家可能都很清楚了。
Q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故事,这家公司后来是如何成为MSH CHINA的?
Patrick:我在2007年遇到了法国MSH的创始人Pierre Donnersberg。当时MSH有很多海外客户,遍布全球,却没办法在中国管理保险理赔,结果亏损严重。而我们当时已经有45名员工了,因此MSH选择我们作为服务商,去和医院谈判,去管理理赔,去做重大疾病的专案管理。仅仅在第一年,我们就成功地将理赔减少了25%,客户满意度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2007年,MSH通过海外收购,走出欧洲,向跨国集团转型,Pierre问我是否考虑被收购。我虽然之前没想过,但我对此并不排斥。于是,Pierre来到了上海,他只讲法语,而我不懂法语。但Pierre有一种特殊的才能——他非常敏锐,凭直觉就能看准人,他知道我们是对的合作伙伴。经过大约六个月的谈判,我们达成了协议。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收购暂时搁置,直到2009年交易才得以完成。2011年,MSH拥有80%的股份,我们仍然持有20%。2017年,我们将最后20%出售给了一个中国买家后, Celine和我决定继续为公司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很享受工作。
Q 我听说,在中国,外国公司中50%的股份必须要归中国投资者所有?
Patrick:这是误解,你完全可以建立一家100%外国公司拥有的公司,在中国叫做 “外商独资企业”。虽然我曾做过很多后悔的选择,但我一生中最明智的决定,就是在中国业务开始时,我给了这家公司一个中国面孔,而不是西方面孔。人们知道我是联合创始人,但我从来都不是CEO。
Q 您退居幕后,与您的NGO工作背景有关吗?
Patrick:不完全是,其实跟我性格有关。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当然,内向永远不是一个负面的评价。虽然我喜欢和人打交道,但我不需要别人的恭维。我可以从内心汲取力量,实现内在的自洽。我依然记得,当我1976年加入天主教救济服务机构时,有个理念我很认同——我们的工作不是去环游世界,展示我们有多么伟大,而是脚踏实地地去做善事。很多美国人会自信认为,自己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但如果你想在中国取得成功,你必须谦卑,努力适应中国市场规则,而不是希望中国人去适应你的规则,这也是许多西方公司失败的原因。我们MSH CHINA,从一开始就做了很多调整,扎根中国市场。
Q 现在中美之间一直存在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关系,您公司是否感受到?
Patrick: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在中国上海没有受到差别对待。恰恰相反,美国人受到了舆论鼓动。特别是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来,在年轻人中间出现了一些变化,以前西方年轻人来中国生活几年,还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显然,在美国人眼中,中国变得过于成功了,让美国感到害怕了。
Q 您曾在援助组织工作多年,然后转向金融保险行业,这两者似乎非常不同。
Patrick:最近我们在巴黎,和Pierre Donnersberg、Christian Burrus 、 Frédéric Grand都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对Christian说:我已经年过七旬了,和Pierre一样,我们仍然在工作,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具有社会意义。
十几年前,我们的客户在中国的黄山爬山时心脏病发作,我们竭尽全力帮助他。我们在山脚下安排了一辆救护车,把他送到最近的医院。但他的情况太严重了,当地医院医疗水平有限无法施救。于是我们马上在附近的大城市(杭州)找能救治的综合性医院,同时安排了一位北京的医生,全程和两家医院沟通病情,远程评估转运的安全性,最终安全转院。我们还派了一名有护士背景的员工,带着大笔现金从北京飞往杭州,帮他垫付医药费和沟通当地一切的琐事。毫无疑问,如果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他都可能救不回来,让我们遗憾终生。我从不期待回报,因为做好事本身就是一种福报。这就是我的信条,也是我们公司管理的理念。